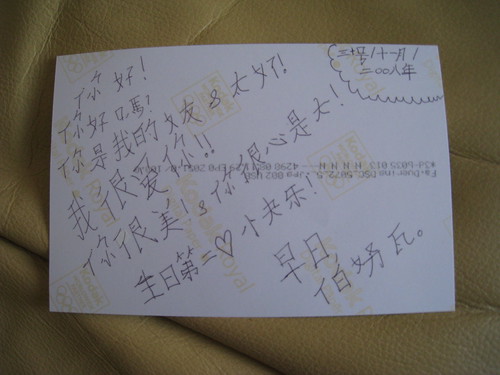星期一早上返工好危險,尤其我這種在火車前線衝鋒的人。
那天我沒有防備下,大清早六時在 Bielefeld這地方上了車。火車坐滿了人,才醒起是星期一。德國很多人住在 A 城,每天 commute去 B 城上班。也有不少人住 A城,每星期一 commute 去 E 城上班,星期五才回家。
於是我提高警惕開始工作,因為那滿滿一車裏盡是受不住「週末已過,又到星期一」的打擊而心情低落、內心空虛、腦袋閉塞、甚或憤世嫉俗的人 。突然有一男子雙眼奇小,呼着口氣問道這車停不停「Düsseldorf 機場」,我回不停,要在 Düsseldorf 轉車。他首先 loading… loading…然後站在那當了機 。過了一會,男子仍陰魂不散,又重複他的問題。我有一刻思疑是自己錯了,還去車長那裏考證。男子這才如夢初醒,走去同事 A 那去駡。事源他較早前未瞓醒地問同事 A 車停不停「機場」,而那車確是停法蘭克福機場的,於是同事 A 答了「Ja」就中招了。同事 A 太輕敵,做我們這行的一定要猜透客人心思,必要時舉一反三,先可避免食死貓。
可是説時遲那時快,我也失守了。一身形龐大、年近四張女子自上車後一直在睡,快到科隆時她醒了,向我點了杯綠茶,還有禮貌地告訴我她有張贈飲劵。由於好得閒,我很快地把茶端上,還附上温馨提示「茶包才剛放進去的」。然後她卻臉色大變,目露兇光,大喊: 「我説過茶包要分開上的」。我呆了一秒後好天真好傻地答:「您有說過嗎?我沒聽到呀!」她嚴厲解釋因為這綠茶一定要精確無誤地放熱水裏一分鐘,不然會太苦,所以她要親自放,想必還會出動 stopwatch。我心裏當然舉中指,但面上卻先是詫異繼而苦笑,然後咁你想點呀? 雙眼誠懇地注視着她,但我並沒有打算換杯新的。最後我這位尊貴的頭等乘客秒秒嘴算了。
這時通道上突然躺着個年輕西裝友,面青唇白,原來剛才休克了,旁邊剛好有個醫生,叫他最好繼續躺着,雙腳墊高。車長立即聯絡了科隆的救護人員來接他。
約九時,車到達了科隆。月台上人山人海,原來往慕尼黑的車已經遲了一句鐘還不見影踪 ,一群傍惶無助的乘客蜂擁而至,又是一輪問答環節,而且是多語頻道。其中不少人問自己預約了的車卡在那裏。
説到車卡位置不得不略談一二 。在月台上其實是有車卡位置圖張貼出來的,但並不一目了然,時常有人站在那板前思索良久。當廣播説車卡次序逆轉時,大家就更加迷茫。如果是ICE 3列車就更大鑊,因為通常是由兩組列車合成。由於兩組車中間不相通,上錯一組車就去不到自己預約的位置,可能付了近百歐羅卻要站幾粒鐘或坐地下。其實只要有帶個腦,坐過一次就明白它的運作。次序倒轉不就是車頭變車尾罷了;如是ICE3就要留意是哪一組車,廣播會說明車卡編號的。
對於老人家、遊客我理解他們的難處,他們語言不通、理解力較慢。但其他的不帶腦又事先不問人,等到車來了才發驢騷。當天就有個女人在科隆對我説:「你們這垃圾鐵路公司害得我每次也上錯車卡!」每次?!即已不止一次?那為甚麼不從錯誤中學習,卻每次上錯車每次怨人?
説會當日,因要等待救護人員來帶走車上暈了的西裝友 ,同事 A站在一車門前阻擋着其他人上車,以確保通道暢通。他着所有人 用別的門,這裏會有救援工作,然後竟然有位阿姐好嬲地問,咁用邊度門呀?!架火車咁長,有 N 度門,係咪咁難揾第二度門呀?!
等了近廿分鐘,救護人員來了,我們的車也因此延誤了。
然後又到星期二。